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影响
发布时间:2019-11-10 09:54:47作者:普门品感应网一、汉地佛教是藏传佛教的来源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自元以来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但汉地佛教是藏传佛教的来源之一。不探其源,难明其流,因此,在介入主题之前,有必要追溯汉地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据藏文史料《隆钦教法史》记载,早在第二十八代藏王拉脱脱日年赞时(约公元4世纪)就有汉地僧人来到了吐蕃:
这位国王(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期,吐火罗与和田的两位译师,邀请汉族堪布李贤到吐蕃,向国王宣讲佛法。由于吐蕃当时没有文字,于佛法无从修习,亦不能传播。李贤遂让国王以具足五佛矩之佛像为身所依处,以《百拜忏悔经》和《无垢顶髻经》为语所依处,以金塔为意所依处,均以五佛印加持,并嘱王向诸宝祈祷,而后返回汉地。……据说汉地盛行并翻译了《般若》、《解深密经疏》和《大圆满》等佛法。吐蕃国王之所以供奉并祈祷佛塔,是为了其国政兴盛、其身能享用二世寿命之故。从印度传来佛法,从汉地请来法师,佛法遂在吐蕃产生。
如果这种记载属实,则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可向前推进两个多世纪。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及部分僧众。根据《柱间史》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作为她的陪嫁带来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佛经360卷、卜算书籍300卷、60种工艺书籍和医药书籍等。
我有所供释迦像,……以此赏赐我娇女,……经典文集三百六,烹调手艺三百六,饮料配方诸多种,坚硬铠甲三百六,锋利兵器诸多种,皆以赏赐我娇女。……汉地秘算三百种,能示休咎命运境,以此赏赐我娇女。……各种医方四百四,望闻问切诸医书,此皆赐予我娇女。把此八万四千法,还有无数智慧海,诸多经书和集解,舍弃十恶修十善,行此六度摄四摄,一切正法亦赐汝。
虽然这些数字有待核实,但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和大量的佛经却是不争的事实。
此后,汉地佛教僧人前往吐蕃者源源不断、络绎不绝。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
沙门玄照,太州仙掌人也……。途经速利,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尼波罗国,蒙王发遣送至吐蕃,重建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
玄太禅师……永徽年内取吐蕃道,经泥波罗到中印度……。
道生法师,并州人也……。以贞观末,从吐蕃路往游中国……。
这些汉地佛教僧人从中原路经吐蕃到天竺,取经学法。吐蕃便成了印度佛教输入中土的中转站。
藏文的很多佛教经典是译自汉译佛经。据藏文古典史料《拔协》记载,在赤松德赞时已将汉译佛经翻译为藏文:
禅呷来高、拉龙鲁功和郭高木莫功等三人做汉文佛经的翻译,以琼保孜孜等做他们的助手;又请来汉地法师玛香麦郭翻译汉地佛经。
这样,从汉地不仅传来了佛像、僧人,还翻译了佛教经论,佛法僧三宝皆具。
此后(公元781年),汉地禅师摩诃衍那从沙洲来到吐蕃,宣扬不做恶业亦不做善业,任何亦不思维既可顿悟的快速成佛法,深受吐蕃百姓喜爱,于是皈依者风靡,而信奉印度中观渐门派者则寥寥无几。这样印度佛教花开花落,每况愈下,而汉地禅宗则蒸蒸日上,人气旺盛。后来出现了顿渐之争,为了一决雌雄,藏王赤松德赞以顿渐两家辩论的胜负来抉择两派佛教在吐蕃的去留问题。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在辩论中汉地法师败北,被迫离开吐蕃。印度佛教被定于一尊,一统天下,成为当时强势意识形态。赤松德赞王下令,今后不得修习摩诃衍那所传之汉地禅法。应修学龙树之大乘中观论。摩诃衍那等汉地禅师们虽然完全离开了吐蕃,但摩诃衍那的“心任何亦不作意”禅宗思想却对日后藏传佛教一些宗派的教义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熏习。这在许多藏文史籍中都有记载,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他的名著《一切宗派源流与教义善说晶镜史》中说:“心要派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噶举派相同,即大手印的表示传承”。阿芒·贡却坚赞在他的《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一书中说:“大手印及大圆满之名称虽不同,修习者们在修习时任何亦不作意,与汉地摩诃衍之(思想)相同”。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他的《三律仪论说自注》一书中说:“后期灭佛法,汉地法师(摩诃衍那)之教理,虽仅依字义,然彼之本名隐去,立名大手印,现时之大手印,基本是汉地之禅法”。
以上史料说明,摩诃衍那的汉地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不是表面的,他的“心任何都不作意”的思想可谓是浸染、渗透到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的深层结构之中了。不仅如此,就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年轻时也曾一度钟情于摩诃衍那的禅法,如《一切宗派源流与教义善说晶镜史》中说:“(年轻时的宗喀巴大师)心中颇满足于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之见”。由此可见,汉地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可谓不绝如缕,绵延不断。
在很多情况下,两个民族在相互交往和接触的过程中,其两种文化的辐射和借鉴是互动的、双向的。汉藏两地佛教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便是最好的证明。汉地佛教延伸到了藏传佛教中,藏传佛教也同样辐射到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大规模的影响汉地佛教是在元代。
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蒙古王室阔端在凉州举行会谈,最后达成一致:西藏归入蒙古版图,藏传佛教可以自由地在蒙古地区传播,蒙古王室率先皈依藏传佛教,并做藏传佛教的施主,阔端支持萨班为藏传佛教各宗派的领袖。在行政事务上,由蒙古方面指派人员来管辖;在宗教事务上,则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来处理。1西藏纳入元代版图,为汉藏两地佛教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修持方式的影响
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内地后,其密教修持实践方式对汉地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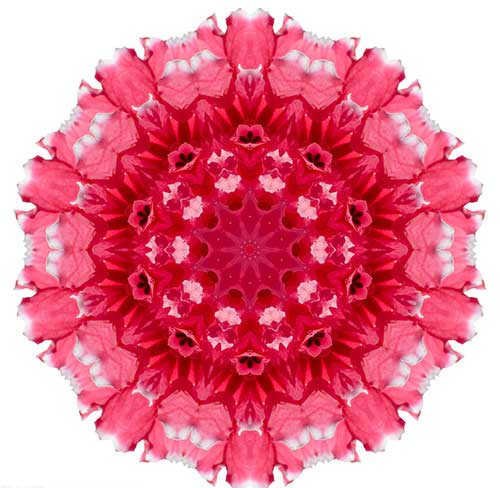
其一,藏传佛教密宗修持实践的一些藏文术语已译为汉语。如:“镇雷阿蓝纳四,华言庆赞也。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也。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笼哥儿,华言风轮也。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2这些藏传佛教密宗用语不仅为汉地佛教所接纳,其修法间或也受到某些人的青睐。如明代杨朝凤的《重修兴教寺记》中记载:嘉靖庆阳兴教寺之“庆沙弥相传而僧讲演揲儿法,尝寓居阇黎方丈。每偏袒升座,一时僧俗川涌云集,率皆举手加额,争趋空门,自寻觉路……。”
其二,藏传佛教密教的一些仪轨传入到汉地佛教中。如八思巴曾为僧众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并就此亲笔写了序文,并由弹压孙和哈达萨哩都通译为汉文。说:“大元帝师苾刍帕克斯巴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亲制序文曰:原夫赡部嘉运至四佛释迦文如来利见也,大元御世第五主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太光孝皇帝登极也。……爰有洞达五明法王大士萨斯嘉班迪达名称普闻上足苾刍帕克斯巴,乃吾门法主,大元帝师,道德恢隆,行位叵测。授兹仪轨衍布中原。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观演说。正本翻译人:善三国声明辩材无碍含伊毕国翰林承旨弹压孙。”
其三,汉地佛教由原来的重显轻密到显密圆融、性相融会。元代以前,汉地佛教中也有密宗流传,但未能传播开来,尤其是其修持仪轨至唐末即湮灭无闻了。元代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密教修持方式的传入,汉地佛教其他宗派便从原来的重显轻密发展到“显密圆融、性相融会”了。这种倾向的出现,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记载是受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但它是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与藏传佛教不无干系。元代藏传佛教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其领袖人物被封为国师、帝师,总领全国宗教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汉地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关注是必然的。因为藏传佛教地位的升降,将关系到汉地佛教门楣的兴衰。在元代,藏传佛教倍受元王室的宠爱,就意味着汉地佛教在元王室中的失宠。
其四,藏传佛教的“方便与智慧双运”的修持方式在汉地佛教中也引起了回应。藏传佛教各宗派大多讲双修,即在显乘方面经过次第修学,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即要转入密教的修持阶段。密教的双修法门虽因各派的理解和传承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其主旨却是相同的。即通过观想佛父佛母本尊而生起大乐并试图恒久住于此乐的一种修持法,意在达到方便智慧双运。如噶举派的密教大手印圆满次第修法就是“从明点修‘哞’,从‘哞’缘待主尊佛父母修,从生殖轮明点出现大乐轮空行母等,逐渐发向意轮、语轮、身轮和三昧耶轮,开发智慧。依止智慧手印反复修炼,能证悟大手印”。然而,在密教双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即少数人借助双修之名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如桂鲁·迅努白说:“时处末法时代,比丘放纵者多。”这种现象在汉地佛教界也引起了反响。如白莲教有《辩明双修》一文,其观点影射的就是藏传佛教密教双修:
双修者,修福修慧也。教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福慧二庄严,乃能成正觉。”……。
今有一等愚人,常行异教,诈称莲宗弟子,妄指双修,潜通淫秽,造地狱业,迷误善人,沉迷欲乐,甘堕险坑岂不谬乎?……今劝在家菩萨依戒修行,勿犯邪非,清心寡欲,双修福慧,回向西方。龙舒(龙树)云:“修福又修慧,深信念阿弥,当生上上品,决定更无疑。”其或不然,欲饭蒸砂徒费力,担柴入火定殃身。
从这段材料来看,一方面,藏传佛教密教修持方式已经波及到白莲教,另一方面,很多白莲教众反对藏传佛教的密教双修法,并用正名的方式给以了驳斥。
综上所述,元代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传入内地,在汉地佛教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汉地佛教学者对藏传佛教的修持方式持有不同的态度,有的非常重视,不仅将一些藏文的修持术语译为汉语传播开来,而且还将修持仪轨译为汉文流布于汉地佛教之中,在汉地佛教中出现了显密圆融的倾向;有的持反对态度,攻击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不合汉地传统。但不管持何种态度,藏传佛教的修持实践对汉地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从汉藏文译经的对勘看汉藏佛教的互相影响
至元二十二年春,元世祖命释克己等奉诏“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忝对楷定大藏圣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汉藏文佛经对勘工作。此举的缘起是由于元世祖崇信藏传佛教,常躬听汉藏高僧讲经说法,自己也于“万机之暇,课诵”,耳濡目染之中,参禅修行之后,念蕃汉传译之殊,疑经教音韵有异,故命汉藏名僧进行对勘佛典。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中说:“大佛法由汉唐以迄于今,揭日月于齐明,致乾坤于泰定,弘济群迷。出生众有,不可得而云:喻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万几之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又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罗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齐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
《佛祖历代通载》中说:“帝(元世祖)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
元世祖想通过对勘彻底了解和理清汉藏文所译佛教经、律、论的基本状况。例如有些经、律、论如果汉藏文都有译本,则勘对其经文是否相同;经文相同,则注明藏文本同,并指出所对应的译本。如“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四百卷(七十九品)与蕃本《十万颂般若》对同;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七十八卷(八十五品)从四百一至四百七十八卷与蕃本《二万五千颂般若》对同”。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汉藏两种《大般若经》译本的对应会、卷。如果没有藏文本,则注明蕃本阙。如“佛于王舍城鹫峰山说八卷(十七品)从五百六十六至五百七十三,此会经蕃本阙”。汉藏译本相同的,则书其梵文名于前,并说明原因。如说:“般若部总四十部七百九十四卷。梵云:麻诃钵罗(二合)提亚波罗蜜怛(二合)苏怛罗(二合),今此总录于题目内间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来三藏,但以梵文译为华言,所以不存梵名,间有存者,于五义中亦有具一二义,故不翻者也。”
通过对勘还指出了从汉文本译为藏文本的佛经、汉译本或藏文译本所阙佛经的数量等情况。如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或五十卷),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等译(初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于阗三藏宝叉难陀译(第二译),此二经同本异译,此经蕃本从汉本译出。”。又说:“第十六会,王舍城竹林园中白鹭池侧说《般若波罗蜜多分》八卷,从第五百九十三至六百卷,此会与蕃本二千一百颂般若对同。此大般若经总二十万颂,西蕃本惟有十六万四千五十颂,若比汉本少三万五千九百五十颂。”
此外,对勘还特别指出:由藏文译为汉文的主要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一卷,八思巴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戒本》一卷,八思巴译。《新译戒本五百部》,八思巴译。《彰所知论》,八思巴造,沙罗巴译。另沙罗巴所译的藏文其它佛典有:《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念诵仪轨供养法》、《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陀罗尼经》、《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各一卷。
从至元二十二年春到至元二十四年夏,汉藏两族佛学大师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作,仔细斟酌,认真勘对,终于将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佛经分门别类、次第编排,勘对完毕,编写出了一部汉藏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通过对勘,得出了汉藏佛经虽部帙充栋,卷轴累屋,然“文词少异,而义理攸同”的结论。这便基本上摸清了汉藏佛教经、律、论译本的家底和见、修、行的实况。
通过汉藏文佛经的对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开启了汉藏佛经对勘之先河。元以来,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交流进入了一个高潮。元代大一统的局面和元王室的崇佛,为汉藏佛教的广泛交流和深入沟通创造了便利条件。从此,汉藏两地的佛教使者你来我往,绵延不断,使汉藏两族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叙录中所说:“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阐,未有盛于此也”。明清以来,承元代之余绪,组织了汉藏佛经的对勘和刊刻。如明永乐年间曾在南京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万历年间刊刻了《丹珠尔》。清代刊刻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大藏经》。这都是元代佛经对勘影响的结果。
其二,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的诞生,是汉藏两族人民精诚合作而结出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一大硕果,它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从思想文化领域里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样一体格局。
其三,它是中国佛教学者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弘扬做出的一大壮举。佛教虽产生、形成、发展在印度,但其完整的结果却保存在中国,作为原创的佛教,在印度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汉地佛教基本上接续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中观、唯识思想,藏传佛教则完整地秉承了大乘佛教中、晚期的思想和密宗的理论和实践。并且将其基本经典翻译成了汉文和藏文。就《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问世,使我们不仅了解了印度佛教经、律、论的数量、内容、思想演变等状况,而且还可以通过汉藏两种译文的对照和比较,来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庐山真面目,以及汉藏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以此方法来理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复杂内涵,其学术价值十分重大。
其四,丰富、填补了汉藏佛教经、律、论的不足。由于汉藏佛经的对勘,基本查清了汉、藏文佛教译经的底本。一些兼通汉藏文的佛教翻译家则把藏译佛经和汉译佛经互无的经、律、论翻译出来,从而填补了汉藏佛教经、律、论的不足。
总之,正因为藏传佛教于元代大规模传入内地,出现了两地佛经对勘之壮举,汉藏佛教学者对汉藏文佛经的内容、版本等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四、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建筑、绘画、雕塑的影响
元代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在建筑、绘画、雕塑方面的沟通与交流,给后世留下了很多文化珍品。
在建筑方面:尼泊尔人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到内地传播佛法,留下了许多尼泊尔式和藏传佛教式的建筑杰作。如北京的白塔,就是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元代在北京建造有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护国仁王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源延圣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藏传佛教寺院10余座。此外,“西及成都,南至杭州”,都有“西藏化的佛殿佛像”。
在绘画方面:由元代最终完成的宋影印《碛砂藏》中,有八幅木刻佛说法版画,更是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宗教文化交流的印证。宿白在其《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一文中有如下论证: 这八种版画所绘形像,除所记汉装供养人、汉装道士和部分天部外,皆所谓“梵式”的吐蕃式样:如佛鬘上置宝严、广额方面、耳垂扁长、肩宽腰细、多作转法轮印:菩萨耳佩圆形优波罗花,体态窈窕; 高僧内著覆肩背心,或戴左右各垂长耳的萨迦帽等。其中人物面相宽扁,表情板滞,佛背光文饰繁缛,背光之后的靠背设大鹏、鲸鱼、兽王、象王四龛,菩萨白毫或作长形等,更具14世纪萨迦寺院形像的特征。因此推测碛砂扉画主要部分来自萨迦,但经杭州汉族画工、刊工重摹雕木时,或有增改,故序号3、4、6、7、8扉画中杂有汉装人物。
在雕刻方面: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因发掘故宋赵氏陵墓,戕杀平民、强抢民女,攘夺财物而臭名昭著,但其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曾在飞来峰主持雕刻了“飞来峰密教石刻雕刻”。其中多是有藏传佛教特点的龛像。如第一一、一六、四五、五七、六五、六七龛的坐佛,第一五龛的倚坐佛,第二二、二四、四六、四八龛的菩萨坐佛,第六四龛的胜母佛像,第五二龛的尊胜塔,第四、五、六龛的护法像等都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之特点。山东长清大灵岩寺的大元国师法旨碑,碑文下半部为汉文,上半部为藏文。陕西富县松树沟的元代时刻,其“主像为三座佛,十六罗汉,这类题材旨在宣扬密教供奉的大日如来。……其形象具有蒙古人、藏族人的特点”。北京妙应寺舍利塔、河南辉县白云寺的普照禅师塔等也都是元代建造的藏传佛教式样的舍利塔。
据此,藏传佛教式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在元代大规模流传到内地,与内地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汉藏合璧的佛教建筑群落,成为今天内地靓丽的文化景观,它是汉藏两族人民智慧的象征,也是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合作的历史见证。
五、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僧侣政治地位的影响
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及其僧众,在元代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元朝允许自由传播的诸宗教中,藏传佛教不仅优于道教、伊斯兰教、也里可温教等,而且也先于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还高于佛教中的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之前,其他宗教派别的位次已经排列分明:佛教,道教,也里可温教,答失蛮教,白云宗,头陀教等。在蒙元皇帝的圣旨、诏书中都是这样排列的。如《元典章·礼部六》中说:“法师、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每根底,多以立着衙门的上头,好生骚扰他每,么道说有为那般上头,除这里管法师的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管法师、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等各处路府州县里有的,他们的衙门,教都革罢了。”浙江温州的也里可温教徒在随朝庆贺时,班次抢在佛道的前面,遂引起佛道的强烈抗议,告到礼部。礼部最后下文:“随朝庆贺班次,法师、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6及至藏传佛教受宠之后,藏传佛教便取代了众教之尊的地位。由于蒙古王室上至皇帝,下至王公,皆于藏传佛教尊崇有加,其他教派与之相比,则黯然失色。就是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也因其教义粗俗、仪轨简陋、功能单调而失宠。在佛教本派中,初期统领天下释教的国师都是汉地佛教僧人,如海云禅师和那摩禅师。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后,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一直在元朝居于国师之位。
其二,帝师拥有很多特权。在朝堂上有专座,为皇帝、后妃授戒时,皇帝、后妃也要顶礼膜拜。出行或还朝时,要举行大规模的迎送仪式。太子即位之前,要帝师授戒。至于赏赐和封号,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元史·释老传》中记载:
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昭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昭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弛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昭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
《草木子》中也说:
世祖以八思麻帝师有功,佐平天下,意其类当代有天下,思为子孙长久计,欲阴损其福,而泄其气,于是尊其爵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丰其养至于东南数十郡之财不足以资之。隆其礼至于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隶。甚而为授记,藉地以发,摩顶以足,代马凳子以脊。极其卑贱。及其既死复于西方再请一人以袭其位。事之一遵其制。”
《南村辍耕录》中记载,皇帝即位前要由帝师授戒九次,才能正式即位。帝师的追加封号与其他官员不同,如八思巴被追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并为之广建佛塔佛殿。如元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泰定帝时“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俾塑祀之。”即使用于帝师的诏书也非同寻常。如《南村辍耕录》中说:“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锈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不仅帝师一人荣登高位,帝师的“兄弟姊妹皆列士”。如《元史》中说:“虽其昆弟子姓之往来,有司亦供亿无乏。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至于给帝师的赏赐,则更是不可胜数。
其三,帝师以外的藏地其他僧人也给予特殊待遇。元王室不但使帝师及其左右亲信享有特权,而且特为藏地的一般僧人制定了优厚的政策。例如《元史·释老传》载,不得侵占僧人田产、不得在僧人居所居住,不得向僧人征派供应、乌拉差役,属于寺院的土地、水流、水磨等,任何人都不得夺占。自忽必烈颁布《优礼僧人诏书》以后,元成宗也颁布了《优礼僧诏书》。其中规定:“ 今后,如有俗人以手犯西僧者,断其手;以言语犯西僧者,割其舌。自颁发此诏书之后,对不敬奉僧人和践踏寺院和寺院的人,请派遣到各地的官员和僧人长老者联名奏来,朕知后必加惩处。”对藏地僧人礼遇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在元代,藏传佛教及其僧侣的政治地位基本上居于众教之尊,无出其右者。如此显赫的地位,其他宗教派别自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就是同属佛教的汉地佛教之地位也与之大相径庭。自魏晋以来,除“三武一宗”等特殊时期以外,汉地佛教一直与儒、道并驾齐驱,成为官方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在政治上一直居于显赫地位。藏传佛教的传入,元蒙统治者对其过度推崇,尤其是对密教修持的偏好,打乱了原有的宗教排序,使汉地佛教在政治上有所失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一种宗教的兴衰,与统治者的好恶有很大关系。

六、结 语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影响了自元代以来的汉地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显密合璧的教法,渗透到了元代汉地佛教中,致使此时的汉地佛教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显密融合的走向,但它在汉地佛教的空间中没有获得更多的扩张。这一事实表明了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自元代以来一直是你来我往,互相交流,彼此沟通,共同促进,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两足鼎立的面向。这说明,佛教成了汉藏两个民族交流和沟通的纽带,这便从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了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藏族的历史事实。
其二,藏传佛教的流播,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纵观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从华夏传统文化到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辉煌,是由于不断吸收、转换、融合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结果。藏传佛教在元代大规模传入内地,不仅是把大乘佛教晚期的见地义理以及金刚乘修持实践的方式介绍到汉地佛教中,更主要的是把藏传佛教文化注入到多样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更加斑斓的色彩。
其三,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并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藏传佛教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编辑:小月



